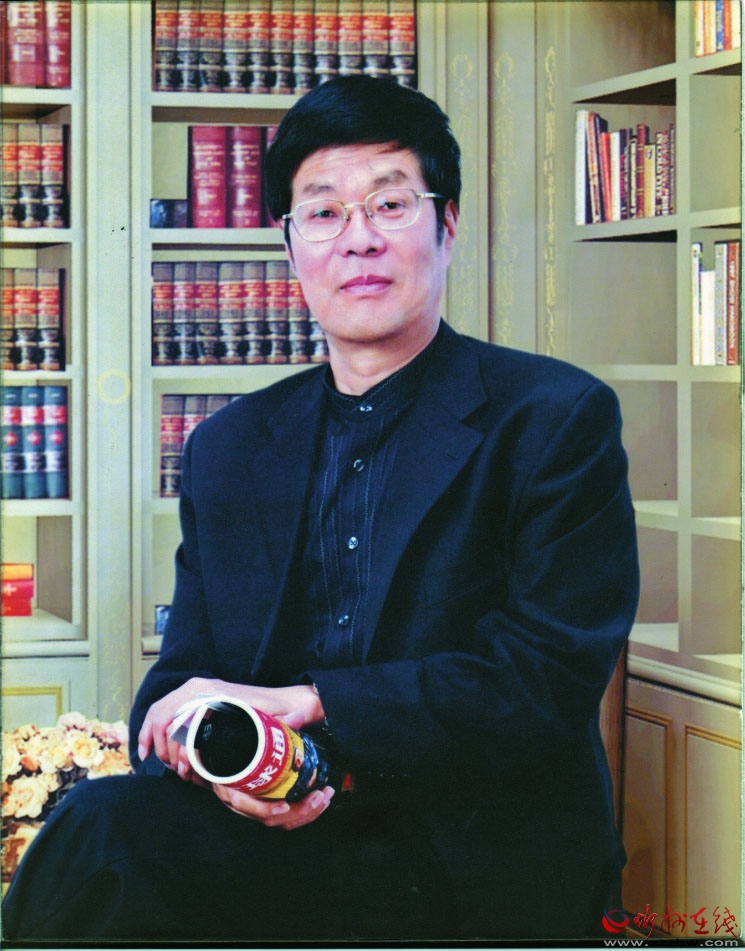
2001年1月,我从忻州市文化局局长任上,调到当时还是总编负责制的忻州日报社担任总编辑。这在外人看来属于“调任”,在我内心深处却觉得是“归队”。
我曾在河曲县委通讯组由干事到组长工作了10年,主要任务就是组织、撰写反映河曲县各条战线推动工作的新闻报道,陪同中央、省、地市新闻单位的记者采写河曲县发生的重要新闻事件和先进人物。10年间,我同上级新闻单位的记者一起走遍了河曲的山山水水,共同采写了诸如轰动一时、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配编者按刊发、被写进中央一号文件、以苗混瞒为创始人的户包治理小流域的重大新闻。基层通讯组的工作人员当时没有记者证,但在我心中,却总是以一个“新闻人”自居。
来报社前,社会上的普遍反映是,报社文化人扎堆、人员的综合素质普遍较高。接手工作后,我对此感同身受。报社同仁甘守清贫、乐于奉献,工作繁忙却从不叫苦叫累。绝大多数同事与人为善,互相理解、彼此宽容,他们献身党的新闻事业的精神和情怀令我感动——而所有这一切,也正是我这一届忻州日报社各项事业兴旺发达、报社声誉越来越好的基础和根本保证。
不过,来报社后,我也深刻认识到制约报社、报纸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和瓶颈,当时的忻州日报社,也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在上级领导的理解、支持和报社同仁的积极配合下,大家同心同德、攻坚克难,办成了几件实事。
一是“差额”改“全额”。报社本来是“全额事业单位”,我接手前因为种种原因改成了“差额”。一字之差,令报社过日子也成了问题——人员工资有时也不能按时发放。报社工作清苦,采稿子的长年风尘仆仆,编稿子的经常通宵达旦,作为报社的当家人,我绝不能让大家在如此辛勤付出的同时还担心“菜篮子”和“米袋子”。为此,我和班子成员多方奔走、反复陈情,“秀才人情半张纸”,终于赢得了上级领导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将“差额”改为“全额”后,大家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得到根本保证而欢欣鼓舞,重新焕发出干事创业的热情和干劲。
二是新建采编大厅。报社以前的工作环境是各自为阵,一个编辑部一个办公室,编辑记者都还在“爬格子”,效率低下,远远不能适应新世纪、新媒体的需要。我同报社一班人反复研究、考察,多次向市委、市政府、宣传部、财政局领导汇报。争取回专项资金后,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先在广电大楼院内西侧建起使用面积400多平方米的采编大厅,然后在大厅内布置电线、网线,设置单人工位,每个编辑记者配备电脑,一举实现了写稿、提交、审稿、排版一体化。所有采编人员彻底告别了纸与笔,实现了当日新闻次日见报,大大提高了新闻报道的时效性。
三是“黑白”变“彩印”。2000年以后,省级报纸陆续上马彩印设备,报纸的版面特别是照片变得清晰、生动。采编大厅建成投入运作后,忻州日报社再接再厉、一鼓作气为印刷厂更新换代,在山西省地市级媒体中率先实现了报纸的彩色印刷。彩印后的报纸图文并茂,面目焕然一新,报纸的档次和品位大大提高,报纸的传播效应大大增强。
四是创办《忻州日报·文化旅游周刊》。一份报纸的“副刊”比正刊更能吸引读者的眼球。《忻州日报》以前的副刊刊名“星期刊”,侧重于休闲、娱乐。忻州文化积淀深厚,旅游资源丰富,在山西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把原来的“星期刊”副刊更名为《忻州日报·文化旅游周刊》,在办刊宗旨、方向、目的等方面作出重大调整。在周刊采编人员的辛勤努力下,《忻州日报·文化旅游周刊》一纸风行,迅速赢得了领导的肯定和广大读者的喜爱,20多年后的今天仍是报社的品牌。
五是抓发行,报纸发行量倍增。《忻州日报》从创刊时的四开四版周二刊,到改成对开四版的周五刊,再到彩印后的天天有报,随着报纸体量的增加,发行量也水涨船高。但发行量的增加只是纵向比较,跟兄弟地市党报的发行量相比,《忻州日报》的发行量依然偏低。我们发动报社全体员工大打一场报纸发行攻坚战,一方面千方百计提高报纸质量,用新颖的版面、鲜活的内容吸引读者。另一方面畅通发行渠道,充分发挥县级通讯组的作用,把报纸发行的“责权利”捆在一起。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报纸发行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期发行量由我上任时的一万几千份增加到两万五千份。忻州每个行政村都订阅一份《忻州日报》,市委、市政府的声音得以及时传达贯彻。发行量上去了,报纸的广告收入也随之大幅提升。忻州日报社成为人们所说的“好单位”。
时光流转,二十多年转瞬即逝。在《忻州日报》创刊40周年之际,作为报社曾经的一名主要领导,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一个单位、一项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坚守初心使命,长征接力,薪火相传。人生短暂,能在五年多时间内谱写一段精彩华章,今生足矣。(王自量)
(责任编辑:卢相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