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一个闪光的名字,他不仅是忻州星空中最耀眼的一颗文曲星,后世评价其高处不减杜甫。关于元好问著作的版本,在他所处的金元时代已广为流传,元好问也因此被誉为“一代文宗”,从元人严忠杰辑录第一部元好问诗集,明人李瀚重刊遗山诗文集,清人施国祁、万廷兰、张穆的元遗山诗集注,再到当代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传承有绪,可以说范本不绝。
然而,“笔墨当随时代”,如何在信息化的快节奏新时代,以当代眼光审视和解读古代典籍,寻求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深度契合点?在中宣部支持指导下,由国家图书馆编纂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重点项目之一《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简称《百部经典》)陆续出版,所选图书上自先秦、下至辛亥革命,包括哲学、文学、历史、艺术、科技等领域的重要典籍,其中元好问著、狄宝心解读的《元好问集》荣列其中,无论从原著本身价值还是解读示范作用上来说,都为我们留下了值得推崇的创新实践与真知灼见。
为什么狄宝心成为“解读者”?
忻州是元好问的家乡,人们往往把一个历史文化名人与一座城市联系起来,这有助于增加这座城市的文化内涵,也有助于对乡贤人物的纪念、研究和传承。早在上世纪80年代,在时任忻州师专中文系主任刘泽的牵头下,省市有关部门大力支持,元好问学术研究曾达到一个高峰。1985年,第一次全国元好问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忻州举办。同时,忻州积极筹备成立元好问研究会,力争把忻州办成元好问研究的资料中心和研究中心,“不仅具有地方性、民间性,而且具有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由此为新时期元好问研究联络了一批知名学者,并及时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学术人才,狄宝心正是借助这个平台走上研究之路。
狄宝心,曾任忻州师范学院(忻州师专前身)元好问研究所所长、中文系教授、古代文学省重点扶持学科元好问与辽金文学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中国元好问学会会长、中国辽金文学学会副会长。他在近四十年的学术生涯中,致力于元好问文献的全方位整理及研究,成果丰硕,专著有《元好问年谱新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元好问诗词选》(中华书局2005年版)《元好问诗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元好问文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等。
正是缘于狄宝心在元好问学术研究中的突出贡献,《百部经典》将《元好问集》列选,选择了狄宝心成为“解读者”。从目前已经出版的60种看,入选的历代诗文别集有10种,分别是唐以前1种,陶渊明集;唐代5种,李白、杜甫、王维、韩愈、柳宗元5人别集;宋代3种,欧阳修、王安石、辛弃疾3人别集。唐宋以后,目前只选了《元好问集》1种。国家图书馆张毕晓在给狄宝心的邀请信中这样表述:“……在最近确定的书目中,《元好问集》入选,通过文献调研、咨询相关专家,并经编委会讨论通过,大家一致希望您能担任解读人。”
2022年9月24日,在山西大同举办的线下线上中国元好问学会第九届年会暨辽金元文学学术研讨会上,中国辽金文学学会副会长查洪德教授对狄宝心解读《元好问集》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下一步元好问学术研究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希望。他说,“我们研究元好问,研究辽金元文学,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考察历史上的民族交融。狄宝心教授出版了一部著作,是他导读的《元好问集》……这对于元好问研究来说,无疑是大好事,但同时也是压力与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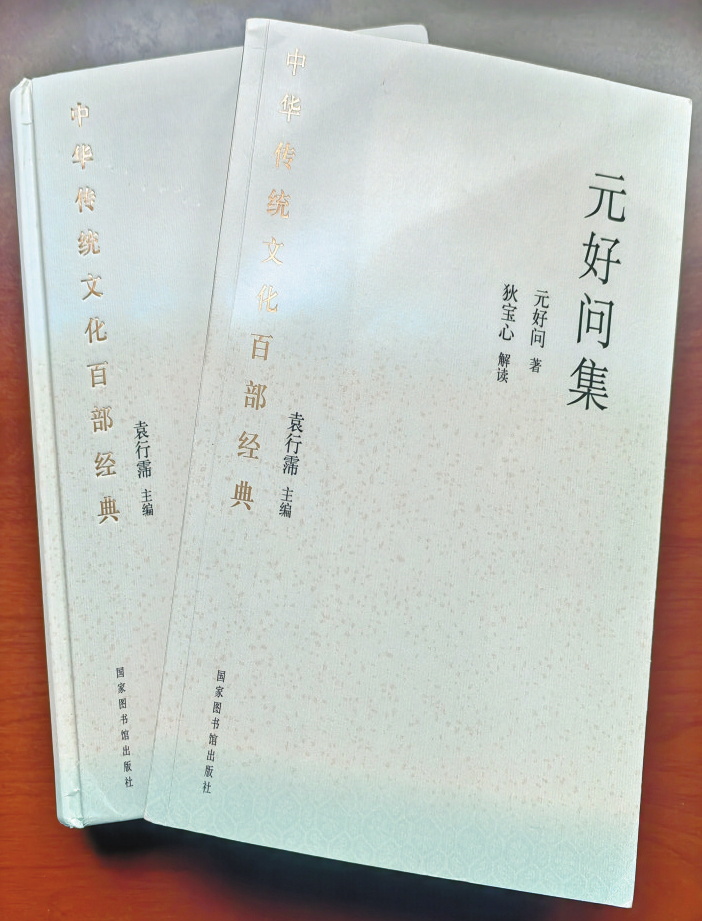
封面
“命题作业”中的精彩解读
导读、点评、旁批和注释这几种形式虽然是《百部经典》系列著作总的体例规范,有点像是命题作业,但是具体到某一部古代经典作品,这仍是一件非常专业、细致、繁琐而又艰巨的工作,需要解读者站在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创造性表达,对经典原著进行简明扼要的导读,画龙点睛的点评,生动精妙的旁批,准确可靠的注释。狄宝心正是凭借着始终坚守的使命,娴熟的文献功夫,壮心不已的学术精神,为读者遴选了一个元好问作品的新版本,帮助读者走进经典的同时,也把元好问学术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祖上是东北的森林民族,是北魏鲜卑人拓跋氏贵族的后裔。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中将拓跋氏姓改汉姓元,北魏灭亡后,有一支落籍于河南汝州,五代以后又迁居山西平定。元好问的高祖元谊,曾在北宋宣和年间任忻州神虎军使,曾祖元春在靖康末年从平定迁忻州成了忻州人。祖父元滋善,生父元德明生三子,长子元好古、次子元好谦,元好问最小,到元好问这一辈在忻已是第五代,可以说是真正汉化的“中州人”了。元好问对自己的成长经历曾这样说:“士之有所立,必藉国家教养,父兄渊源,师友讲习,三者备而后可。” 可见他的成就与早年受父辈及兄长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狄宝心《解读本》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对元好问作品的关键节点和精彩诗词文赋进行的点评。在许多读者的印象中,元好问“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的词句最为熟知,这首千古名作也是元好问现存最早(16岁)的词作。点评开头的文字概括精练,有画龙点睛之妙:“有人因词而知名之效,这主要得力于首二句,它既是对人世生死取向的深层灵魂拷问,也是对‘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价值理念的奋力高扬,故特别有必要对首三字异文的取舍细加申述。”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该词《摸鱼儿》的首句究竟是“问世间”“问人间”还是“恨人间”,或争论,或模糊,或矛盾,狄宝心《解读本》给予考证和认定,应该为“问世间”。一、三卷(最早的版本)作“恨人间”,四卷作“问人间”,五卷本《宛委别藏》作“恨”,张家鼒南塘本作“问”,姚奠中李正民增订本据《全金元词》改“问”为“恨”。他认为酌改理由有三:一是“老翅几回寒暑”问的就是大雁。“君应有语”四句指殉情的大雁对词人的答话,故前二句显然是问句,应作“问”而非“恨”;二是下选同属早期且被誉为双璧的《双蕖怨》词,首二句也作“问莲根、有丝多少,莲心知为谁苦”。宋人张炎《词源》中说:“《双莲》《雁丘》等,妙在摹写情态,立意高远”,指的就是在艺术思维上将动物、植物拟人化进而设问对答,以我观物,融我于物。可知二词的思维模式如出一辙,首字应为“问”;三是词序已将大雁殉情的凄惨事例交待清楚,怜悯惋惜之情酝酿得满满的,“问世间”就像火山喷发,词人的满腔疼爱感伤喷涌而出,有大堤溃决汹涌澎湃、一泻千里之势,如作“恨”则是将满腔激情咽回肚里,然后像剥茧抽丝一样娓娓道来,在艺术爆发力上大打折扣。至于“世”与“人”的问题,发“问”者是词人,被问者是大雁,“世间”包括雁,若作“人间”就是问人而非问雁了。再者咏物贵在物中有我,我中有物,不即不离,如作“人”则是离物,直接写人,失去言在此而意在彼、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这样的解读既忠实于原作,又能给读者拨云见雾般的感受,使读者对元好问原著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其例子不胜枚举。
元好问是中国文学史上继唐代杜甫之后又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作之所以获得后世如此高的评价,这与他的那些丧乱诗作有关,其中金亡前夕所作的《岐阳三首》成为其丧乱诗作的开端,也代表了遗山诗的主要特色与最高成就。正大八年(1231年)正月,蒙古大军围攻凤翔,二月攻破屠城。其一首句“突骑连营鸟不飞”,指陕西军事重镇凤翔府所辖岐阳,被蒙古大军的铁骑及营帐层层包围,连鸟也难以飞越,其诗句脱胎于杜甫《潼关吏》“连云列战格,飞鸟不能逾”的诗句。其二“十年戎马暗秦京”本杜甫《愁》“十年戎马暗万国”;“岐阳西望无来信” 本杜甫《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西忆岐阳信,无人遂却回”;“野蔓有情萦战骨”本杜甫《遣兴三首》“朽骨穴蝼蚁,又为蔓草缠”。在一首律诗中如此密集地化用杜甫诗句,可见杜甫诗对其影响之大。“元好问深沉悲凉的感情基调、百转千回反复咏叹的表达方式、苍凉壮阔的意境及字字如重锤撞击心扉的千钧笔力,与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完美契合。此后元好问沿此一脉顺势而发,撰就了一系列声情并茂的‘丧乱诗’,形成了他‘笔力苍劲’‘声情激越’‘沉郁苍凉’的诗歌风格。”元好问原诗的精妙与狄宝心的精彩点评,互相映衬,相得益彰,可使读者对元好问作品有一个深度的理解。

书引
超越时代的“中州观”
元好问自谓“诗人元遗山”,这是其自我定位,他认为自己的诗歌成就高于其他,实际上他是诗人、词人,是历史学家、散文学家、笔记小说家,也是一位思想大家。
狄宝心作为解读者,在“导读”中重点从三个方面对元好问的思想给予了深刻解读,尤其是对“以王道仁政定正统不辨夷夏”的观点与胡汉文化互动互补,对中华文化共同体之“中州观”作了更为明确而独特的解读。
在蒙金朝代更迭的大动乱、大变革时代,元好问写下了大量关注民生疾苦、记录时代的丧乱诗之后,开始思考千百年来存在于中华大地的先进文化文明的延续。当时辽朝称宋为南朝,以北朝自居,也自称中国。元好问本属鲜卑族后裔,生长于女真蒙古政权以及胡汉共处的忻州这片土地,他属于非传统型的文人,“贵夏贱夷”的观念十分淡薄,共处互补的中华文化共同体在他身上体现得却十分明显,对此他引以为荣:“白塔沉沉插翠微,魏家宫阙此余基。”“魏帝儿孙气似龙”“元氏从来多慷慨”(耶律楚材《和太原元大举韵》)。相对来说,元好问的视野比较开阔,更容易接受辽、金、元执政者所倡导的一体多元、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优势互补理念。其“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 (卷十一《论诗三十首》),对北朝敕勒民歌尽情赞美,认为《敕勒歌》吸收了汉魏以来雄浑苍莽的英雄气。他缅怀“神功圣德三千牍,大定明昌五十年”(卷八《甲午除夜》)的文治,对金“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金史·文艺传序》)的文学成就特别重视,称金中期以来胡汉文化交融所成就的文坛巨匠蔡珪、党怀英、赵秉文为“国朝文派”(《中州集》甲集第一《蔡珪传》)。
元好问最著名的作品《中州集》就收录了女真、契丹、渤海等族的诗人之作,冠名为“中州”,在诸族之上赋予了更高层次的中华文化共同体之义。家铉翁《题中州诗集后》:“壤地有南北,而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虽在万里外,皆中州也”(苏天爵《国朝文类》卷三十八),认为元氏命名的“中州” 不是地域方位概念,而是以“道统”“文脉”为基准的,与“道统、文脉无南北”有内在联系,旨在强调超越种族歧视,唯贤不唯亲,认可中华各族之先知先觉的“天民”都有继承道统、文统正脉的正当权利。
狄宝心在“导读”中吸收大多数学者观点,“其中遗山最先意识到保护儒士的重要性,以文坛盟主的身份上书耶律楚材,觐见忽必烈,并在蒙古上层及汉人世侯间进行了长期大量的活动,为新朝保护、培育、输送了大量人才,功效最著。这些认识与行动,与当时士人以救世济民为真儒之主流价值取向的形成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可以说他顺应时代的需求,又反哺于时代,引领了时代的潮流”。
元好问深知王朝更迭的时代大势,以“沧海横流要此身”的历史责任感,写下了大量诗文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云南山高去天尺,汉家弦声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清映南极。幽并豪侠喜功名,咄嗟顾盻风云生。今年肘后印如斗,过眼已觉乌蛮平。谕蜀相如今老矣,不妨铜柱有新名。”在这首元好问《刘时举节制云南》的七律诗中,解读者狄宝心对元诗精辟的“旁批”是其一大特色和贡献,这为普通读者阅读原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首四句突出多民族中国理念的认同,说明蒙古不畏山高路远而大一统之举。此“汉家”非指汉族,与中国“中夏”“中华”的含义基本相同。次四句:凸显刘氏勇于进取的威猛之气。末二句:期待刘氏多些劝化的仁爱之心。“损有余,补不足,恩威兼顾。诗人用心良苦!”最后在“点评”中肯定了元好问对元帝忽必烈大一统的观点。“在中国进入十三世纪后半叶初期之际,元好问明察秋毫,高瞻远瞩,在这首诗中顺势大声疾呼,表明了‘九州之外更九州’的中国疆域观、尊重民生以王道定正统的中华一统观。”
经典古籍、历史文化名人,也要走进今天人们的精神世界,也要今天的人们可以读懂。作为《百部经典》之《元好问集》这样一个文化发展工程,就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可以说是经典中的范本。经典的文本,加上解读者狄宝心精心选取的精华部分和精彩的解读,深入浅出,明白晓畅,让优秀传统文化贴近现实生活,走进人们心中,以文化传薪火,这便是这本书最值得阅读并予以热心推荐的理由。(张云平)
(责任编辑:卢相汀)